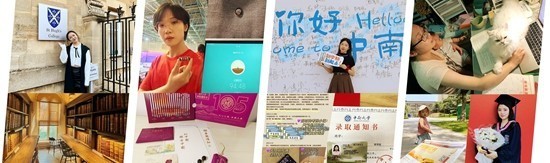
毛佳、寇馨升、秦瓊、李敏虹(從左至右)備考期間和重返校園后的日常生活圖集。受訪者供圖
“重返校園的感覺真好!80后也可以像00后那樣朝氣蓬勃。”35歲的寇馨升如今是南開大學的研一新生,開學后,他迅速“融入校園中”。
最近,已經熟悉新環境的他常約著同為研一的00后同班同學一起打羽毛球,“會有一種穿越感,想起十多年前的自己。現在的我,還是本科時的樣子,我還是那個少年”。
30多歲的年紀,在許多人印象中,應該是人生逐漸趨于穩定的時期。然而,也有一部分人下決心重返校園,繼續深造。
“重回校園不會帶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這段經歷會讓你獲取更多知識,更好地面對一個個未知的挑戰。”34歲的秦瓊說。
30多歲,再做一次學生
當決定從國企辭職去考研時,寇馨升周圍幾乎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
在大家看來,寇馨升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在國企做合約工程師,拿著一份還不錯的薪水;即將續簽無固定期限合同;沒有太大的工作壓力,下班后可以隨時休閑聚餐。
直到一段感情上的變故,他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時,萌發了自我提升的想法,“我離開學校太久了,從事的都是單一工作,感覺自己的綜合能力和素質都在下降”。
恰好在此刻,寇馨升看到南開大學一篇有關錄取通知書里兩顆種子的文章,一句話深深觸動了他,“一顆留在家鄉,不忘初心;一顆帶來校園,見證成長”。寇馨升回憶起自己18歲時對南開大學的向往。他知道重回校園不容易,“現實阻力很大,但要沖就沖自己最想去的學校”。
與寇馨升不同的是,李敏虹是32歲時萌發的重返校園的念頭——“想學習應用心理學”。
本科從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后,李敏虹做過護士,也做過健康管理師。一名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病人讓李敏虹對心理健康問題非常好奇,“那段時間懷孕,我也在想小孩的心理成長是怎樣的?掌握心理學能對孩子成長有什么助益?”
除了理想和情懷,30多歲的他們重返校園也有一些現實的考量。從程序員轉行外企產品經理的秦瓊不是第一次重返校園,她說:“如果我想要換個工作,證明自己的能力,原本的專業背景是不占優勢的,甚至連面試機會都不會有。”
工作后的經濟獨立和一定的儲蓄,也構成一部分他們重返校園的底氣。33歲從某國企辭職的毛佳(化名)說:“因為學的是語言學方向,本科期間就想要出國留學,但由于財務方面的因素擱置了。工作十多年后,攢了一些錢,慢慢地,這個愿望就可以去實現了。”
回到學校的路有多遠
“重回校園的路,肯定不是輕松的。”下定決心后,寇馨升沒有貿然辭職,而是選擇在職備考。上班前、午休時和下班后的閑暇時光,被用于爭分奪秒地學習。壓縮社交和游玩時間,頂著可能失敗的焦慮,這樣的生活,寇馨升過了3年。
“最大的困難在于很多知識‘扔掉’后已經忘了。”寇馨升花了一個多月才解出一道最簡單的微積分題,第一次做英語閱讀理解,只認識基礎詞匯……寇馨升沒能在第一年實現夢想。第二年,他猶豫再三,放棄了一所可調劑的學校后,準備“三戰”南開大學。
已婚的李敏虹面臨著不同的困境,第一年備考身懷有孕,專業課成績很好,但政治差了一分。第二年,她堅信自己一定可以考上,但是受到產后激素波動的影響,一度陷入消沉;作為新手媽媽,她邊備考邊帶娃,差點放棄。“孩子一旦醒來,我就要全身心地照顧,喂奶、換尿片、陪伴玩耍,只能在孩子睡著的間隙學習。”
好在她的丈夫非常支持她的求學計劃,還會幫她一同分析這段時間的學習情況和效率。李敏虹刪除了手機上許多社媒軟件,屏蔽外界聲音。每天,李敏虹都把要學習的內容錄下來,一邊播放,一邊照顧孩子,“鍛煉自己快速切換狀態的能力”,逐漸地走出低谷期。
全國碩士研究生統一招生考試如期而至,初試、復試、層層篩選,時間的車輪駛過期待和焦慮參半的日夜。寇馨升在回吉林的火車臥鋪上看到了南開大學的擬錄取通知信息,他控制不住情緒,給周圍很多人發了消息,一會兒哭,一會兒笑,“那一刻,既有喜悅,也有對未來的迷茫”。
不久后,今年7月15日,寇馨升收到了南開大學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他拆開快遞,取出錄取通知書中的兩顆來自嘉興南湖的蓮花種子,小心翼翼地握在手中。開學前去報到的路上,為防止發霉,他將兩顆蓮花種子封裝在了紙袋子中,一顆放在了家鄉東北,一顆放在了南開大學的寢室抽屜中,持續激勵著自己的夢想。
陌生的環境、陡增的學業壓力和年齡上的焦慮,成為他們重返校園后依然要面臨的難關。
盡管有多年的職場經驗,高強度的知識傳授和陌生的校園環境,也一度讓寇馨升手忙腳亂。“很多知識都是全新的,內容很多,研究方法也是不熟悉的。如果沒有及時鞏固和其他輔助,很難吸收完當堂課的內容。”
寇馨升通過學習、主動交友和運動排解孤獨和迷茫,收獲了“許多一起聊天、散步和看日出的朋友”。
李敏虹也發現同學們都很友好,喜歡和她這位年長幾歲的“姐姐”聊天,聽取她的建議。“抱著學習新東西的心態,其實和年紀更小的同學們沒有什么差別,大家都是剛開始接觸這個領域。”
從職場回到校園后,寇馨升和李敏虹一樣,都更加珍惜這一段來之不易的“回流”時光,“不會再像之前那樣渾渾噩噩,只想著去放松,現在覺得和老師、同學們相處的每一段時光都很珍貴”。
重返校園能否重啟人生
針對“大齡讀研是否值得”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講師謝鑫認為,大齡讀研或留學“一般意味著他們從勞動力市場返回了學校,從創造經濟價值的勞動者角色轉變為積累人力資本的學習者。社會雖然暫時失去了一批勞動者,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國家知識資本的積累,對經濟發展有利。當前,國家通過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來培養大批高層次應用型人才,而有工作經歷的大齡人員是其重要生源。”
謝鑫分析:“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大齡人員辭職讀研或留學是一種個人的教育投資決策,他們一方面需要承擔經濟、時間等方面的成本與機會成本、應對未來不確定的職業前景;另一方面,也能結合工作需要有針對性地提升知識、技能和學歷水平,為自己的職業發展創造更多可能性。”
去年,李敏虹完成了在華南師范大學的學業,目前在一所學校擔任心理教師。此前工作時認識的客戶會向她咨詢心理和身體健康的問題,朋友和親人了解到她所學的專業后,也會時常向她請教。她計劃成立一家心理咨詢工作室,幫助女性處理個人成長、家庭教育和親子關系等方面的問題。“女性在家庭關系中的作用遠比我們平常認知到的更重要,我希望用所學的知識幫助她們。”
李敏虹覺得自己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自我認知”,“20多歲,我覺得一切都挺好的,那時候也沒有太高的認知,但是讀的書越多,就越會發現自己的無知。現在想要的,或是思考的,會比以前更多,想要做的事也不會停留在只為滿足自己”。
出國留學后,毛佳在校園里結識了一位50多歲的同學,“他重回校園是為了興趣,研究薩克斯”。毛佳發現身邊很多留學生“會刻意間隔幾年,再去選擇讀研還是申博。因為國外的學費還是蠻高昂的,工作一段時間,有了一定的社會經驗和明確的規劃,積攢足夠的錢后,再重回校園,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專業,也是很好的選擇。”
“在牛津大學讀書,可能只是我人生中1/40的部分。”如今,毛佳回到長春,沒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回到“老崗位”,繼續從事針對各年齡段的國內外英語考試輔導。
“我不想把自己安排得太累,出國留學就像是人生的一段精彩體驗。”留學回來后,她的生活節奏反而更注重“松弛感”,“會安排更多的時間健身、學習、聽播客,偶爾會在社交賬號上回憶留學生活,分享一下世界各地的旅游攻略”。
毛佳認為:“重返校園就像是忙碌日常里的生活調節劑,我需要它,讓生活變得五彩斑斕。”
“重返校園確實為人生提供了一個新的開始機會,更重要的是怎樣去把握這樣的機會。”李敏虹覺得“重返”的選擇,促使她“有了更清晰的目標和內驅力,更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唐軼 實習生 任哲曦 馮樂妍 來源:中國青年報